

一条战壕 情重千钧
—— 追忆沈墨君在战斗岁月中与南黄海战友二三事(下)
□ 吴 尧
黄山相聚 我们又集合了
1948年5月上旬,当我华东野战军4纵10师扎营黄河北岸,进行大反攻前的休整时,一纸调令,沈墨君另有任用。走前,他赠给我一个小本本,通林纸的,同他平时用的前线记事本一模一样,本子上写着赠言:“三人行必有我师,一路朝前!”
2008年5月上旬,当我的战斗岁月梦似在欲醒欲睡中,辗转反侧时,一封快信,沈墨君从安徽发来,像他平常说话那样,寥寥数语:“人生苦短,相聚难得,来吧!”
原华野4纵10师文工队张家驹⑩、葛焕⑪、魏璇、芮美、吴尧及缪云、周根娣等人,从长江南北应约来到合肥,聚于市区新加坡花园城。花园城逸景阁美仑美奂,一路亭台,一路遐想;一湖春水,一湖诗情,这就是老队长今天的住处。一见面,他的第一句话:我们又集合了!这是一位耄耋老人心灵的召唤。此回,他将带领文工队来自南黄海的小队员,最初结识的小同志,今日的老战友,作黄山及其他古山古水古村落的6日游。沈老的夫人原知名戏曲演员王萍,安徽香泉谷影视城办主任吴萍等陪同。老人心细,顾及全面,他要我们纵情山水,一应资用,他的稿费有备,放心启程。他说,这又是一次行军,是在不同时代,不同心情下的千里行。
感慨地说来,从黄河到黄山,我们苦苦地走了60年。长长岁月流程中的骤变,使我们分别后的行军,没有一个跟一个,走成一条直线,而是各奔东西,各食其果,酸甜苦辣,该有尽有,不该有的也有,如老队长在1957年的遭遇,其时,他正在总政创作组从事笔耕。此组是当时很有声望的一个精英集体,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诸种作家的精英集体。运动反右,沈墨君定为右派。他自言自语,那时他只有自言自语:“命运中该有此一劫。”他这样说,那时他只得这样说。他身在劫中,心并没有成了枯木死灰,心醒梦自来。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大胆用上他,他竟然崛起脊梁背负着一盏辉煌,新作主题形象:一盏红灯。长春电影杂志首发剧名:《自有后来人》。即被上海京剧院看中,将对话改成唱词,定名《革命自有后来人》。接着国家用,改名《红灯记》。作品辉煌了,辉煌得不认原作者。老队长在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口号声中,失踪。从此,沈墨君的名字常在我的记忆中浓墨显示,整整20年,直到邓小平主政,1978年底,我接到来信:
六十年代,我写了电影《革命自有后来人》(后被改成剧《红灯记》)以后,就离开电影界,和中国最广大的农民、集镇的市民生活在一块儿了。我做过木匠,翻卷的刨花像我起伏不定的生活,我当过教师,那些拖着叫哇哇的弟弟妹妹一起来上学的农村孩子们,善良朴实,多少回勾起我的创作欲望。但是我没有动笔。生活对于我,虽已不是宽宽展展的一马平川,也决不是无路可走的断崖峭壁,战争年代有比这更艰难的时刻。尽管,大桶美酒醉不倒我,冰川雪冰也不会把我吓死。我仍旧不能写,被江青点名定性的人,难道还有可能打出十八层地狱重返影坛吗?我的笔沉默着。我的眼睛却不可抗拒地看到了应该看到的一切,一旦压在身上的“雷峰塔”倒掉,这些生活就都洒向我的笔尖。有人云:人老了,我依然对酒当歌!
1982年,《花城出版社》出版了沈墨君的电影文学剧本集,他将此信作为“后记”收在集子中。
读了信,百感交集。人世间,原就在变数中人生演绎。绿叶衰草,都是一种气数使然,天地律化不可免。然而,有一种亲情不变,生死一个战壕的,血浸过的,此种亲情历史的底色浓重,岁岁年年风蚀不化,它植根在心液中。而一量遇上时机,它就会疯长,它就会凸现。听到老队长20年后的声音,原文工队的南黄海人,又复集合起来,依然那样地整队出发,一个跟一个,走成一条直线。
上南昌,在新四军最早的大本营,追初温故。
来南黄海,在掘港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致默,向我们的旅长张震东⑫将军问安。
再赴孟良崮,在一座座曾经战斗的高地阵前,念念当年。
今日又在合肥集合,兵发黄山。11日出发前,老队长说话:
就事说事,黄山是一部书,去读书,是丰富知识,去游山,是愉悦精神。人间重晚晴。要会过日子,更要会用日子。上黄山过日子,将那些知识的,精神的感觉带回来。下黄山后用日子,就用上它,这就是我们的晚晴。
说得多好!我记在心里。取道黄山北麓、南麓。从北口进山徒步几许,有电缆搭乘,每车厢设16座,余则站立。其空间相当大,可容纳80人,看来此16座是专设老者儿童坐的。我们一行年皆70多岁,不去一顾,全是儿童坐了。可是有一小孩走至85岁高龄的老队长面前,拉他坐,老队长摇手,孩子缠住,老队长竟然把孩子扛起让他坐在肩上,自己方去就坐。缆车在半山下客,凭脚力走上千米高处游览站,也有双人抬的竹椅可乘。我们拎脚走上云雾中的游览站,俨若成仙白日升天了,相视而笑。目极处,山路仍然上升,一座高悬着的索桥软梯,顶端架扎九天,蜿蜒中落苍海。从下至上满桥满梯都是各种穿戴的男女,端的花团锦簇深浅色,照在绿波中。这一景观的凸现,给黄山增添了多彩的创意。
老队长挥杖走在前面,山路陡险崎岖,一边悬岩,一边峡谷。我望着老队长那高大的身材,那一身随意长的休闲服,加上宽宽的长裤和北京老布鞋,生发出一种大,大得可以走遍天下说一声:我,堂堂中国人,姓沈名墨君。顿时我思量起60年前,队长年青时,师供给处发给他的军衣难得合身,就是那么短,他照收照穿,不管衣不合身,身不合衣。他说:“只要人是合格合理合情合意穿这军衣。”他就是穿这一身不和谐的军衣忘了自己,唯有弹光与血色,辉煌了他的每一步脚印,带领我们走过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最艰苦时期。那日子同今天欢乐的黄山道,全是两个世纪不同的人生风景。黄山道也有昨天,虽然没有我们的战斗岁月,但那战斗岁月中却有华山,遭受到战争的摧残。都过去了,黄山道两边,悬岩照旧,狭谷照旧。悬岩后的老碑依然,狭谷下的古木依然,这一切都在文人的咏叹下,佳构典藉,那一排排老碑是诗歌的老碑,那一株株古木是散文的古木。中国的民族文化,永远有故态,永远有新意,永远可读,永远美丽,不变几千年。
感叹间,登上排云亭。老队长说:“排云亭前观黄山,才读到黄山的唯一。”脚前峡谷之长之大,视野不及。古木交错,绿涛争鸣,有如苍江十月雷。望远山峰峦叠嶂,行空天马,浑是峰峰青天柱,诸石无不示妙相,形意万千异。都是云也,都是峰也,都不是,都是天工一笔耳!排云亭前,特意竖一景碑提示,那些云朵,那些峰态,注文形容之,或似“仙女抛绣球”,或似“文王拖车”等等。老队长说了声“俗”,我领会其意,他说的是碑上所注文意俗气。他引前人所云“天地毓万物,黄山撷其奇”,黄山所撷之奇,排云亭前绝赏其首。它是由气长起,诸象随目,思之而生,不以固状定格。老队长的指点,我有悟。一句话,黄山情,才是黄山最本真的特色。
老队长见我朝远云注目沉思,问我看出了什么?我说,毫无“文王拖车”感。但是,那朵云果真是形象化了的,酷似一个背着一个人。老队长紧接下言,一个女人背着一个男人,佝偻地走在大雪中,龙卷风式的飘雪围住她,一阵一阵地堵,她是那样地艰难无持,走不上前,说着老队长叹了一口气。我默默地,心里清楚他说的是什么了。他说的一个右派苦守艰境20年中的一次遭遇。
他是从朝鲜前线回来的右派,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文工团的艺术指导,整风中错划为右派,回家乡劳动,用汗水洗擦自己。他只老母在堂,乡亲们不能同他接近。左右邻里远而避之。他苦,干的是厂里最苦的体力活儿,打草,磨粮,摇煤球等,日夜劳动至清晨。就在一个大雪之夜,下班回家。他的住处和厂隔一座大桥,厂在桥西约200多米。住处东巷口转弯身下,有一水井,是他的必经之路。他艰步深雪中,冷也来了,饿也来了,他忍,可是心忍身不忍,走近井边,昏沉沉地跪下,昏沉沉地前卧,顷刻,雪盖没了他。就在50米外的巷西口边,有一间小屋,碎砖墙隔开,前头是邻人灶间,后头是他的宿舍,睡眠时,他就置身满屋是呛人的油气与烟灰中。
厨房使用人是国营厂的一位青年女工。她上夜班,这时也冒了风雪回家,脚脚踏在厚厚的雪中,没有放松步子。寒天是轧花厂的忙季,她被召回去应急司磅,成了忙人,走在路上也在盘算时间,如何得早归早睡早起早来,心热,则一路风雪全成为毋须置疑的事了。路是老路,安知有阻。走上井边,被绊,坐下,她站起,勉强按捺住惊异,踏进家门,她的家就在厨房斜对门,没有掸一掸全身雪,又走进厨房里间看了看。肯定了一件事,井边雪中倒着一个人,她的心在世情上感受了点分量不同的压力。但是,她冲出门,走到井边,下劲扒雪,扒出了人,背起他,扶着沿路墙壁挪动身子,就这样苦苦地走完了50米。
这个被救起的人就是我,救我的青年女工就是我的老伴。当时,她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救起我,我为她胆颤心惊,于是争取活过来,极力坚持活下去。都将近50年过去了,竟然今天在黄山排云亭前,目睹了那段历史的演义,如此形象性地,我被联想的意念猛烈地掴了一巴掌,醒过来,从对“黄山情”的认识中醒过来:“景为黄山有。情在人心中”。
我们走上一条青石铺砌的石级山道,两旁全是苍松翠柏。拾级升阶,缓缓地走向一座庙,黄瓦红墙,檐牙交错,隐在一片竹叶儿萧萧,松涛起伏中。俯首万象如苍海,老队长喃喃吟道:“何用别处方外去,人间亦自有丹邱。”这两句诗正是唐人韩同登山访仙游观所作七律的最后两句,所谓“丹邱”是指海神。跨进庙中大殿,香烟袅袅,地上跪着一平排香客。我发现其中有老队长夫人王萍,还有我的老伴,也都是举香过头,状很虔诚。老队长看了两眼,头点点,走出殿门在石凳上坐下,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:
她们两人也在顶礼膜拜,我相信,她俩膜拜的不是那堆泥,不是那个泥塑金涂的所谓佛,偶具耳!她们是以一颗平常心膜拜心中思念的人。平常心难得,平常心是传统的古道遗世。佛家传承之,道家传承之,儒家传承之,史家传承之,广泛的传承在民间。这大道大德就在平常生活里的平常人平常心中,所以,生活里有常人常事。
老队长说到这里,举了身背的军用水壶喝了一口水,我一眼不眨地看着他,要听他的下回分解,接着,他说了一个小和尚的故事:
一天,有个小和尚问老僧人,“佛是什?”老僧人说:“就是大殿里的东西。”小和尚说:“殿堂里的东西不就是泥土塑的像吗?”老僧说:“是呵”,小和尚听了百思不得其解,又问:“师父,到底什么是佛?”老僧这次具体回答了:“道就是佛。”小和尚说:“道又在哪里?”老僧还是说:“就是殿堂里的东西。”小和尚只好说:“师父,我刚入佛门,听不懂你说的意思,请求师父详细地教我”。老僧问:“你吃饭了吗?”小和尚说吃过了。老僧说:“那就洗碗去!去做该做的事。”小和尚听了,茅塞顿开,原来是这样,“道”在平常生活中。老队长说到这里又重复了一下,“道”在平常生活中,所以生活里有常人常事。
老队长说完故事,我们就下山了。一路上想着老队长的句句入耳话:
大道大德,常人常事。是啊,大道大德,应该成为常人常事。
注解:
⑩张家驹,如东双甸人,岔河参军,文工队总务组长,曾任解放军某部团政委,转业曾任如东县商业局局长。
⑪葛焕,如东人,岔河参军,文工队戏剧组长,转业曾任南昌市艺术团团长。
⑫张震东,1947年2月7日,华中野战军第1师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长

沈墨君、葛焕、周根娣、吴尧、缪云合影

1947年的吴尧与王君平合影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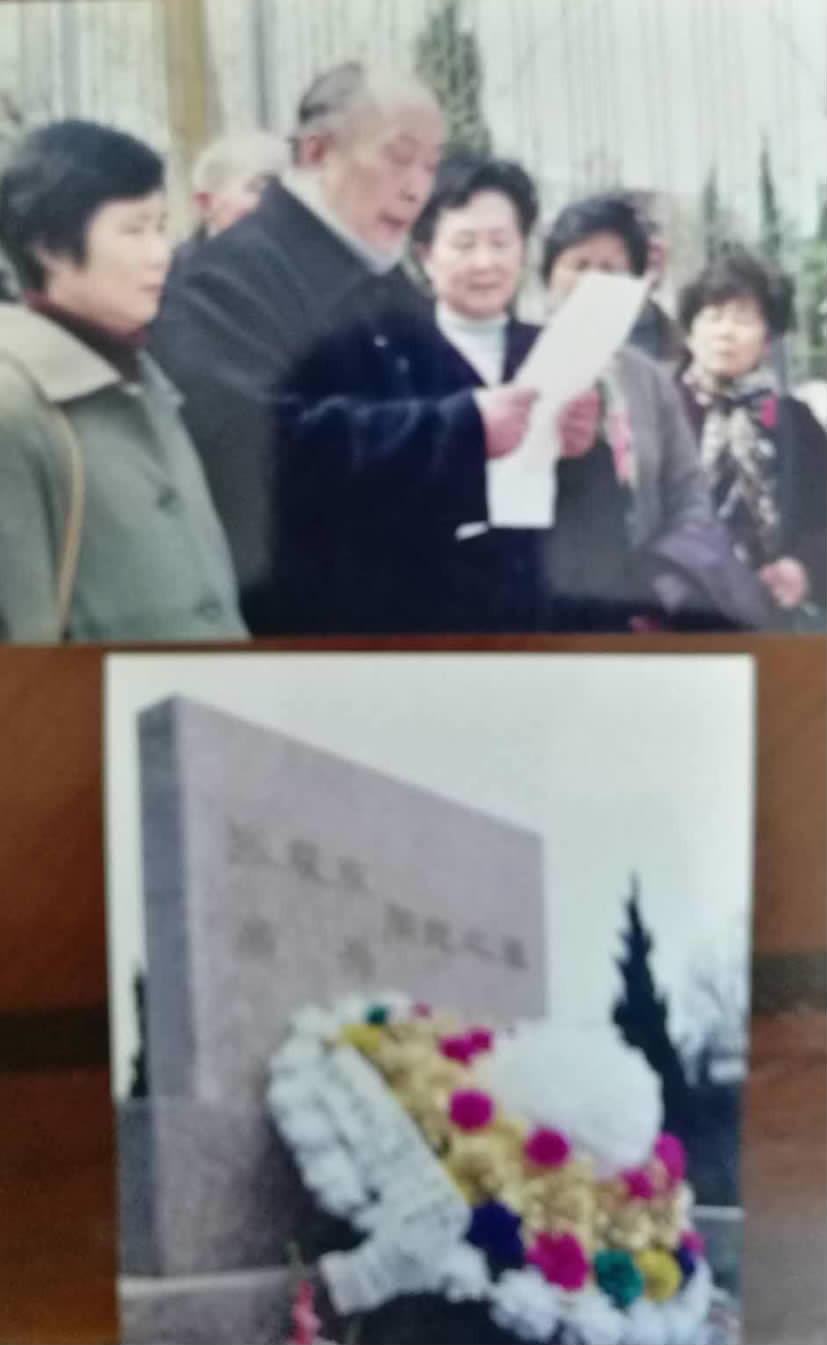
沈墨君在如东吊唁张震东将军

